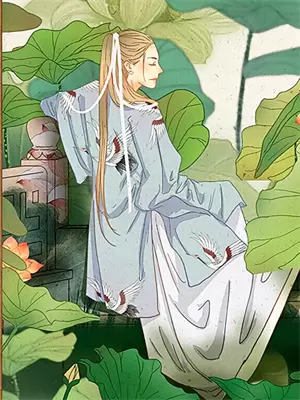内监尖细的嗓音带着哭腔传到凤仪宫。
贵妃和德妃几乎同时站起身来: 是哪位皇子?
先帝停在长生殿尸骨未寒,他的儿子们已经兵刃相接,在京城乱战了三日。
内监哆哆嗦嗦的目光越过诸妃,最后落在我身上: 十一殿下奉旨讨逆。
七皇子呢?德妃顾不得仪态,一把抓住内监的衣襟。
大门骤开。
阴影笼罩了小内监单薄瘦弱的身形,他颤抖着瘫倒在地上——年轻的男人提着长剑,另一只手抓着还在淌血的头颅。
他嘴角噙着一丝冷意,把手中头颅掷向德妃: 七哥在这里,娘娘不用找了。
接着他转过身来,看向末座的我。
鲜血和铁腥浓郁的味道扑面而来,他却温温然地笑,就像我第一次见到他一样。
他冲着我跪下来,说: 母妃,我们回家。
我被送进皇宫的时候才十四岁。
以逾不惑的皇帝用赏玩一只金丝雀的眼光打量了我一眼,问: 你的父亲是荣国公谢祯?
我点点头说是的,就这样进了宫。
我叫谢韫,是从小被以妾妃之德教养长大的荣国公嫡女。
皇帝封我做美人,住在阮淑妃钟粹宫的偏殿。
阮淑妃出身将门,面冷心热,在我宫廷生涯的前几年,一直是她照顾我。
起初我很怕她,但很快,我发现淑妃并不喜欢皇帝,甚至有一点堂而皇之的不屑。
蔺家人,心都脏。
她这样说,眼神透过窗子,望向天边外。
我理解她的高傲,她是将门长女,京城诗书和镇北枪锋撞出的一寸霜,江河照破凝出的明珠,天然就该凌驾众芳。
可我后来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那是我入宫的第三个月,贤妃小产,淑妃与我同去看望。
我和她坐同一乘鸾轿,她的声音清泠泠的,带着点勘破世情的悲哀:
阿韫儿,到了凤仪宫不要乱说话,贤妃的孩子从一开始就生不下来。
为什么?
她叹了一口气: 她是蛮女,天子血脉不容异族混淆。更何况近几年燕北南侵,战乱频仍,如果这孩子生下来,以后是要踏碎母亲的故土,还是挥刀向他的父亲?
不待我问一句倘若是个帝姬——阮淑妃就打断了我。
不可能的。她说,蛮族和中原,不可能的。
鸾轿走到凤仪宫门前,淑妃牵着我下轿,珠帘卷起的刹那,我看见一个倔强沉默的身影。
瘦瘦小小的一个人儿,站在漫天飞旋的雪片里,雪片漫过他的脚踝。
这是我与蔺琰的初遇。
淑妃浑当看不见,抬脚就往正殿里去。我那时候好奇,又多嘴,就问他:
你是谁家的孩子?
他抬起眼睛,冷冷地看着我。
他是一个眼里有凶光的孩子,眼神像多疑的刀,让人畏避。
也只是个孩子。
我见他不想说话,轻轻笑了笑,淑妃已经回头催我,我只能跟上去。
隔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回头望,他仍然站在原地,安安静静地看着我,单薄的身影孤寂如铁。
凤仪宫阴沉沉的。
座上的皇后端庄慈和,却略显出衰老的颓态,像佛堂里的玉观音。
她问: 淑妃,你与贤妃父辈有隙,是否怀恨在心,做得此事?
淑妃抬起脸来,很高傲地笑了笑: 妾与贤妃同为天子嫔妃,燕北与我朝又是议和之时,妾父兄正率军北驻,又岂会出此糊涂之举?
她咬紧了率军北驻四个字,皇帝的脸色就缓和下来,说到最后,皇帝已经全然换上一张温和的脸了,挥了挥手示意她起身。
我忽然想起淑妃在鸾轿上说的话,那孩子生不下来,今日在凤仪宫,只是寻个女人做替死鬼。
看来淑妃不会是这个替死鬼。
可总有一个人是的。
尚宫女官奉旨搜宫,很快在德妃的承乾宫寻出了红花粉。
贵妃撇了撇嘴: 怪不得她不敢来。
却远远听得一声笑,接着是脚步声。帘子一响,进来一位美人,鸾袍凤钗,明眸善睐,顾盼神飞,恍若月宫中人。
是德妃。
德妃柳眉一扬: 方才是谁在背后嚼舌根子?
皇后的脸色冷冷的: 德妃,凤仪宫不是你放肆的地方。
皇后很讨厌德妃那个过于聪明的儿子,连带着这个得宠的母亲一并厌恶。
妾是来请罪的。德妃恰到好处地落下泪来,承乾宫西阁元御女谋害皇嗣,妾为主位,未尽看管之责,请陛下责罚。
贵妃不信: 元氏和你多有龃龉,你说话怎么可信?
元氏出身奴籍,心性低贱,有什么做不出的。请陛下问尚宫大人,那脏东西定然是在西阁被搜出来的。
尚宫女官点了点头。
她每说一句,皇帝的眼神就柔和一分。
他很满意元御女来做这罪魁祸首。
没有审问,不需证据,皇帝显然不愿深究一个女奴的清白。
杖刑,以儆效尤。他轻描淡写地说。
内监带着可怕的廷杖来了。
元御女说她没有罪,不肯跪,他们就把她拉到院中。元氏伏在长阶上,廷杖把她的骨头砸碎血从她的嘴里涌出来。
小黄门忽然嚷起来: 十一殿下,您不能进去。
是那个孩子
他竟然是元御女的儿子。
我和所有人上一起看着他闯进来,那个瘦而单薄的孩子推开阻拦的小宫女,又撞开苍老的内监,跌跌撞撞地跑到元氏身边,深黑色的眼睛不安地扫视着每个人。
他的目光最后落到父亲身上,像一只绝境中的小兽,伏在母亲身上,用身体死死护住她。
皇帝有点厌恶地示意小黄门,他们就把那个孩子拽开,元氏似乎想撑起身抱一抱自己的孩子,但终于做不到。
北风乍起,搅动雪片和绯色的轻纱。
蔺思凡,不要哭。她的声音凄厉痛楚,最后落成一句,你好好的……
我们不忍再看了。
据说那日的最后,皇帝挥了挥手,让人把她的头颅割下来函封,送给燕北赔罪。
据说那女人被拖下去的时候还没有死,我似乎能听见她破碎嘶哑的喊冤声。
据说那时雪片子纷纷扬扬的,后宫很快又是白茫茫的一片,看不出血的痕迹,那个孩子在风雪里沉默着,像一个深宫的怨灵。
我回去就起了高热。
夜里,我梦见流着血的女人,嘴唇一张一合。
救我啊。她声音凄厉,我是干净的。
那时候已经临近年关,中宫恩赏宫人一月俸银,女人们脸上都是笑影,元御女很快就被人忘记了。
但她的魂魄总进我的梦里。
淑妃让人给我炖安神汤: 宫里死人是很常见的事,你不要害怕。
但我的病一直不好,侍寝的事情也就只能拖着,家里着急,父亲与皇帝关系甚笃,私下里问起宫里的女儿,皇帝只是笑笑: 朕会派御医多看顾谢美人。
但汤药始终不见效果。
我的魇病在开春那日,痊愈得离奇。
在那场梦里,元御女冲我柔柔地笑,眉眼弯弯。
不像死时的不甘与愤恨,那日她穿着一身干净朴素的宫装,半旧了。
她坐在我对面,拉住我的手,是暖的:
请你照顾好他。她说。
然后她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梦里。
立春,皇帝下旨,册钟粹宫谢美人为婕妤,抚养十一皇子蔺思凡。
我领旨时,淑妃正翻着一卷《平戎策》,闻言叹息一句: 也算有个依靠。
贤妃扳着指头算了算: 你今年十四,才比他年长七岁,怎么可以做他的养母?
陛下把我的年纪添了十岁,现在我和贤妃姊姊一样年龄。我低头一笑,姊姊,你要恭喜我。
早点把他接回来。淑妃斟了一盏年酒,我在镇北见过失群的狼,那孩子眼神太拗,你不把他看在身边,不知道要出什么样的岔子。
宫女就是这个时候跑进来的,她神色惊惶:
娘娘,十一殿下不见了。
夜雨如织。
找人的宫车沿着甬道疾驰,辘辘如雷。
元氏与德妃本不和睦,担心有人对蔺思凡不利,我在车上心如擂鼓。
直到我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
开门
我一掀车帘,看见蔺思凡站在巍峨的承天门前,正一拳一拳砸在西角门上。
宫人如蒙大赦一般对我行礼: 正要派人回报婕妤,十一殿下闹着要出宫去,宫门落钥,非变不开,让陛下知道又要责罚他,请婕妤把小殿下带走吧。
淅淅沥沥的雨打在鸳鸯瓦上,然后顺着檐角滴落。蔺思凡的手在流血,但他仿佛浑然未觉。
开门。
他的声音已经哑了,放我出去。
我在他身边蹲下,一手用伞挡住细密的雨丝,雨水濡湿了他的额发,我取出手帕替他擦。
他一把打落了我的手: 我要出去。
出去做什么?
见我阿娘。他用那双黑而深的眼睛盯着我,今天是她的生辰。
她已经死了。我说。
蔺思凡置若罔闻,仍旧拼命地拍打宫门: 开门让我去找她
红漆的重铁门闷闷响着,像天上的滚雷,我站起身,静静看着他。
蔺思凡喊得累了,倚在宫门上,大口大口地喘气,雨水从他的脸上滑落。
闹累了,就回家。我向他伸出手,外面冷。
他犹疑许久,问: 你是谁?
钟粹宫谢婕妤。我轻轻摸了摸他的头,现在是你的母妃。
他警惕地看着我。
皇帝的旨意不可忤逆,但是我这个年轻的母妃是可以忤逆的。
我们就这么僵持着,雨丝斜斜地飘落,初春的风和他的眼神一样冷漠,他看了我手中的伞,又看见我匆匆跑来时湿掉的衣裙,然后推开我,默默站进细雨中去。
最后他还是答应跟我走,却拒绝宫人撑伞,也不肯和我同乘一辆宫车,只是慢慢地跟在宫车后,像夜色中一只沉默的幼兽。
你不是我母妃。直到进了偏殿,把热腾腾的姜茶捧到他唇边,我才听到他开了口,还是倔,我再也见不到阿娘了。
凭着这句话,我就猜出他不肯好好与钟粹宫诸人相处。
果然一回去,他就以虚情假意四个字将淑妃气走了。
蔺思凡倔着一张脸,不说话,更没有去道歉认错的意思。
我只好让宫人给他取伤药,自己去正殿劝解淑妃。
淑妃姊姊不要生气。
我惴惴不安,淑妃却早已不见方才的怒气,笑道:
本来还气着,只是想到这孩子很像他的父亲,他父亲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么倔。
淑妃待人宽和,侍女们并不拘谨,也是调笑搅闹,我们聊到兴起处取了骰子做博戏,输家免不得要唱一曲,女孩们就拍着手笑,笑声熨暖宫檐上的青铁铃。
蔺思凡就站在热闹背后荒凉的影中,点漆一样的眼中偶尔露出一丝羡艳。
我出正殿的时候,见偏殿一片漆黑,没有燃烛。
我当是宫人惫懒,正准备笑骂她们两句。
谁知黑暗里迎面撞上一双很可恶的眼睛,吓得我一趔趄,惊呼出声。
是蔺思凡。
我恶狠狠地盯着他: 蔺思凡,你为什么不许宫人掌灯?
可能是我太凶了, 他抱着锦衾往里缩了缩。
我更恼火了: 你为什么睡我的床?
他低着头把衾被乱七糟地团在一旁,站起来的时候又换了一脸无所谓的神情: 我不稀罕。
他睡我的地方,用我的东西,还不肯认账。
我很生气,拿起软枕就作势要打他——横竖是苏绣的枕头,打不死人,但如果他不受点教训,早晚会揭了钟粹宫的鸳鸯瓦。
我气昏了头,忘了我一向把抄来的戏本子藏在枕下,一时藏之不迭。
蔺思凡眼尖手快,一下子抢过去,举得高高的: 这是什么?
我只能吃瘪: 抄的书。
嫔妃也要读书?
我灵光一现: 文德皇后的《女则》,你们做皇子的不用读。
他草草瞟了一眼: 你别打量诓我,《女则》怎么会写陈元礼?
我扑过去要抢,他霍然站起来,展起字纸读: 陈元礼,你快去安抚三军,朕自有道理。
我愣了愣,突然有些大逆不道的错觉。
他真的有点像个皇帝。
我跳着脚去捂他的嘴,他一趔趄,倒在衾被团上,我从他手里掰过字纸,三两下扯碎了,气愤愤地吓唬他: 不许告诉别人,你如果乱讲,我就不要你了。
若他把我抄这些淫词艳曲的事情说出去,不但我要受罚,荣国府也要担上教女不善的罪名。
他好像真的以为我生气了,拉了拉我的袖子。
你别生气。他说,我都收拾好,不劳烦你的人。
我闷闷地在桌边坐下,看着他忙,感觉他又很乖。但他刚才确实像一位天子,眼神可恨,带着帝王家一脉相承的阴冷。
我轻轻哼起那段戏文后的唱词。
魂飞颤,泪交加。堂堂天子贵,不及莫愁家。
蔺思凡铺起床来比宫女还快,我倚着小案哼戏里的调子,他就站在我面前静静地听,不说话,也不离开。
你可以走了,我不生气了。
我没有地方去。他说,我阿娘死了,你看着她被打死的。
我心里涩涩的,我想如果有谁要害我的家人,我一定在他心上狠狠扎个对穿。
可杀死元氏的是他的父亲、天下的主人。
他跪拜皇帝的时候会恨吗?
我突然觉得蔺思凡眼里的怨毒都那么可怜。
你看一下,我弄的很整齐了。
我怔了怔。
他好像觉得我不相信,很认真地解释: 阿娘说,我是女奴的儿子,不配以皇子自居。承乾宫没有人把我看成皇子,我的一切活计都是她来做。
可德妃只要心里有气就骂她,她每天都很累,我就学着帮她收拾床褥,她很高兴,但以后我都见不到她了。
我把你抄的书弄坏了,对不起啊。
这些就是我所知道的全部,关于他过往的七年。
春雨淅淅沥沥的,显得偏殿格外安静。
他本应过两天才会挪来钟粹宫的,但他在承天门一闹,我只得提前将他带回宫里。所幸蔺思凡年龄尚幼,可以不避嫌疑。女官权宜一番,将内室的青纱橱挪给了他。
我一向睡眠很差,今晚更是辗转反侧,雨水滴落,润湿青石板街,每一点细微的声音都像敲在我的心上。
隐约听到蔺思凡也翻来覆去睡不着,就问: 你为什么不睡?
我饿了。他小小声说,我今天没有吃东西。
桌上有点心匣子,你自己来吃。
蔺思凡穿着寝衣,灯影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我支着脑袋看他吃东西的样子,很好奇地问: 你很不喜欢掌灯?
他点了点头: 会感觉安全一点。
这里的宫人都要听我的,陛下把你交给我,你说的话就是我的命令。如果你饿了,就告诉她们,她们不敢不听——是有人怠慢你么?
不是。
小厨房不合心意?
我不敢吃。蔺思凡说,上次有野猫吃了我的糖蒸酥酪,死掉了。
你不怕我害你?
他轻轻摇了摇头: 不知道,我有一种奇怪的直觉,你和她们不太一样,阿娘说孩子的直觉都很灵。
宫里的点心噎人,我思来想去,下床帮他斟了一杯热茶。
他伸手接那盏茶,手一抖,茶盏掉在地上,碎瓷四溅。
他压抑着抽了一口冷气,把手缩到身后。
怎么了?
没事。他扯出一个风轻云淡的笑意,蹲下身要拾那些碎瓷片: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他的手,他手心的伤裂开了,血从伤口浸出来,指背上被也被磋磨得不成样子。
之前的伤。他低下头去,刚刚帮你收拾,裂开了。
你放心。他急着解释,没有沾到你的床褥上,我知道我的血脏……
胡闹。我抓过宫人留下的伤药: 不要乱动。
我展开他的手,用纱棉蘸了药酒,轻轻替他清理着伤口。
药酒蛰人,他本能想往后躲,却仍然努力展着手,眼神低垂。
你不觉得脏么……我母亲是九年前进宫的侍马奴,她们都说我的血脏。
我笑笑: 十一是很好的孩子,不要妄自菲薄,人若是自轻自贱,旁人就更看不起。
我想了想,又补充: 我会保护你的,替你阿娘。
他沉默很久,然后抬起头,无遮无拦地看着我。
我不会让你像她一样。他很认真地说,你等我长大。
我想他是透过我看到了他低贱却温柔的母亲,那些话也不是对我说,我的护佑是谢氏宗族,不会是一个执拗瘦小的孩子,但我只是替他用缠带覆好伤口,碰了碰他的脸颊。
还是小孩子,多笑一笑,不要在心里藏太多事。我把他送回内室,又替他掖好被角,他安安静静地看着我,在我转身离开的时候,忽然笑了笑。
谢婕妤。他轻轻说,晚安。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笑。
平白多了个孩子,很辛苦吧。淑妃悬腕落笔,雪花宣上墨点飞溅,字如游龙,不似寻常闺阁娟秀字体。
他很安静,也懂事。我摇摇头,只是眼神太凶,心里又盛着很多事,连我也不告诉。
我心里涌起一点酸涩。
你自己也是个孩子。我和你一样大的时候,还在镇北骑马,哪里懂得照顾人?
她用笔杆轻轻敲了敲我的眉心: 让我听听,我们阿韫儿发现他什么秘密了?
淑妃姊姊上次的点心匣子是哪里得来的?我低下头,他很喜欢吃,但不愿意找我要……他最近胃口不太好,整日不爱吃东西。
你对他真好。淑妃笑,那是薛婕妤的手艺,她是宫里最会做糕点的女人。
薛婕妤?我闻言皱眉。
这名字我并不陌生,薛氏双姝是瑶州令的女儿,姐姐红颜薄命,生育长乐帝姬时难产,很早就过世了,妹妹进宫那日天气晴朗,西角门抬出了姐姐的棺椁。
但她并不如自己的姊姊讨喜,女人们说她攀高枝的心太重,世族妃嫔说笑的时候会提起起她,一个节食到成为宫中笑柄、过分纤瘦并渴望皇帝宠爱的女人。
但淑妃不讨厌她: 你带十一去薛婕妤宫里坐一坐,长乐生得灵气,又讨喜。他们小孩子间,或许能有话说。
我回偏殿的时候,蔺思凡正坐在廊下撕书,他把字纸撕成细长的条,团成团子打雀儿。
敬惜字纸的道理,没有人对你讲么?
我有点生气,先生说过,撕书是大不敬的事。
他抬起头,认认真真看着我: 没有人教过我。我是侍马奴的儿子,不能进国子监。
我很惊讶,我单知道奴隶所生子女未及束发不入玉牒,不晓得连读书都不许。
那你……识字么?
他点点头。
写你的名字给我看。我蹲下身,把手伸到他面前。
他犹疑着,伸出手指轻轻碰了碰我的手心,又很快缩回去,我看见他的睫毛微微颤动。
我阿娘是洗马的女奴。
我知道。
你还是不要碰我了。我手是脏的,血也是脏的,你是世族的女孩吧……你和她们一样,都那么贵气。
他用那双黑而倔强的眼睛盯着我,仿佛要剜出一个答案来。
我也静静看着他。他忽然站起来,眼睛似乎要把我穿透:
我不要你可怜。你不喜欢我,就不要装出一副伪善的样子。
你既然不听我的话,我为什么要喜欢你?
他一怔。
我早就告诉你,人须先自重,旁人才不能看轻。风把他的碎发吹到颊边,我伸手替他别到耳后,云淡风轻道,何况我是你母妃,就算全天下都用刀对着你,我也会站在你这边。
他默默抓住我的手,指尖轻轻划动,痒痒的,像一只小猫在挠。
他写字的时候很认真,唯恐出错,但那本来就是不对的。
燕北蛮文。
你不会写中原字吗?
蔺思凡低低地说: 我阿娘这样教我。
我读过一些书,虽然不比宫里的夫子,但也能教一教你,等你懂得多了,我就求陛下让你去国子监,和你的哥哥们一样。
他点了点头,又有点惶惑地问: 我听人讲,女子无才方是德,但你读过很多书。
身躯已经不能自主,心不能再做奴隶。我小声叹了一口气,握住他的手,想吃那晚的点心匣子么,我们去延禧宫看看薛婕妤和你妹妹。
他忽然甩开了我的手,很紧张地笑了一下: 我认得路,我……我自己走。
他在前面跑,把我和宫侍甩得很远,但我分明看到他在每个仪门前停下,若无其事地回头看,我冲他笑,他就转过头去,跑得更远了。
薛婕妤宫里的点心像流水,小小的,像一个个玲珑的梦。
她其实是个安静温和的女人,眉眼淡淡的,手拢在鲛绡纱的大袖里,袖口用金线绣着桃花,并不像传闻里的狐媚。
我品了半块绿茶酥,长乐乖乖把茶盏推过来,我呷下一小口茶汤: 薛姐姐,你这手艺是哪里学来的,怪道小十一总想着。
我没有。蔺思凡捏着一块槐花紫霞糕,看着我纠正。
好,是我念念不忘,非把小十一带来的。我笑吟吟地推了推他。
薛婕妤也笑,声音柔柔的: 我父亲在任上纳了一个姨娘,她每年做很多糖水,也有酥点,样式从来不重,我是和她学来的。
我小时候很喜欢吃糕点,长乐也喜欢,你要是觉得好,就常过来。
可惜现在已经不是花期了,味道差一些,以后你一定要多来延禧宫。
我有点怀疑地看着她,她标致而清瘦,身段轻盈,弱柳扶风一样,不像是嗜甜的人。
她很娴静地抿唇笑: 我小时候圆滚滚的,每天都要吃两碟糕,阿爹说我和姐姐以后都要入宫,不许我再吃,不然就要打。其实我也不敢吃——天下男子谁不喜欢身段纤瘦的女人呢?我怕我再吃下去,陛下就不喜欢了。
薛婕妤指着一碟枣泥山药糕: 这一碟糕,我只敢吃一口,也不许长乐多吃。我的手艺奴才不配用,剩的丢掉也就罢了。
我心里不是味道,我觉得。
但很快我就不太伤心了,因为长乐捡了满满一匣子糕点捧给我。
她小小一个女孩,捧着一个大匣子,献宝一样: 这是长乐送给婕妤娘娘的,娘娘笑起来真好看。
我低头温温然勾起唇角: 长乐嘴真甜,婕妤娘娘最喜欢长乐。
我回宫的时候就要入夜了,宫车摇摇晃晃的,蔺思凡坐在我身边,冷冷的。
他从延禧宫出来就不大高兴,冷着一张脸。
我把点心匣子在他眼前晃晃,逗他说话: 十一你看,我诓了好多点心,都给你吃。
我不要。
你怎么啦?我拉了拉他的手,他把手抽开了。
他的眼睛像无底的渊水: 你是陛下给我的,对不对?
蔺思凡并不喜欢称皇帝为父亲,总是规规矩矩地喊陛下。
但我分明记得有一天,我带他去御花园放风筝,正撞见皇帝与德妃母子游园。他就看着皇帝和兄长的背影出神,一直到他们头也不回地消失在淡金色的阳光中,繁花满径,欢声笑语像银铃。
我轻轻应了一声,他转头看着我,宫车轧过青石板,像隐约的雷声。
只是给我的,对么?
我想了想,皇帝应当不会再让我抚养其他孩子,就点了点头。
那你应该只喜欢我,不可以喜欢长乐。
这不一样。我分辩。
他不说话,安安静静看着我,目光沉默而执拗。
理会一个孩子的胡闹是没有意义的,于是我揉了揉他的头发,软声说: 那我只喜欢十一,十一也要听我的,多笑一笑,十一笑起来很好看。
他似乎没有听到一样,不笑,也不动。
宫车驶到钟粹门前的时候,他掀开车帘跳下去,回头看着我的眼睛: 我不是不爱笑,我只是讨厌一个人笑。
阳光猛烈,青石冷清。
我们都是这样的人,伤心的时候一个人哭,开心的时候,也只笑给自己看。
我抬头,宫阙之上,万里无云。
今年的巧夕宴格外热闹,嫔妃脸上都挂着体面的笑容,但身在宫闱,笑影里就难免有些凄凉。
美人们把一支胡旋舞成泛滥的风情。
蔺思凡搅着碗里糯白的米圆子,头也不抬。
你不喜欢过节么?
到处都是笑影,我逃不开。
我贴在他耳边,小小声说: 可你现在有我啊,我陪着你,你不会孤单的。
他用力点了点头: 阿姊对我最好了。
我纠正他: 不是阿姊,是母妃。
阿姊。他坚持。
我正待要同他细细解释,他却忽然扯了扯我的袖子: 你看,薛婕妤。
那时候我还很年轻,并不了解宫廷。在薛婕妤之前,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位骤然得宠的妃嫔。
见我很难将娴静纤弱的薛芷与艳冠群芳的宠妃联系在一起,即使传言说,她为了皇帝的宠爱,可以整日只食花露,以保持身段的轻盈。
女人们像绽放的牡丹花瓣一样散开,花蕊处的舞姬用雪白的手臂擎起铜盘,像补天的娲神。
薛芷轻盈地立在铜盘之上,翻飞的彩袖让她成为宫城中唯一的蝴蝶。她的出现使得冗长的歌舞迸裂四散,又在短暂的鼓乐声中达到了高潮。
她如愿赢得了皇帝的青睐,从她出现的那一刻开始,天下最尊贵的目光再也没有离开她。
她的苦心孤诣为她带来了泼天的荣华,皇帝当场敕封她为昭仪,又打破了帝姬食封不过三百五十户的规矩,将长乐帝姬的食邑加到五百户。
皇帝的眼神几乎迷狂,像是发现了遗落多年的奇珍。
朕今夜宿薛昭仪宫。
可是,陛下已经定了谢婕妤……皇后轻声提醒。
皇帝只是有点不耐地挥了挥手。
是的,内监宫宴前传旨,今晚本应是我侍寝。
真是妖媚。贵妃的笑容流露出一点居高临下的骄矜。
她是皇后的胞妹,一向以高门贵女自居,举手投足都是贵气,一双桃花眼透着近乎刻薄的精明。
陛下快取一把金锱赏薛昭仪。她眼睛一眨,女人们也就跟着笑起来。
这是京中赏花魁的俗例,花魁献艺后盈盈一福,小倌就捧出一个铜盘,客人们抓一把金锱或银毫掷进盘中,叮叮当当地作响,叫做金锱绝赏。
皇帝也很有兴致,真的让成喜托了一盘金来,宫人恭顺地将铜盘举过头顶,他很随意地掷了一把金锱,那些精巧的东西闪着光,蹦蹦跳跳地落在地上。
谢陛下赏。薛昭仪盈盈一拜,唇边含着得体的笑意。
皇帝愈发高兴: 你们也来。
于是贵妃就拈起一枚金,向薛昭仪抛过去,德妃也笑着,从手上取下一个鎏银戒子,随手扔过去,那枚戒子被烛光映得一亮,弹到地上,一跳一跳地滚远了。
这是莫大的羞辱,用赏赐花魁的礼节对待世家女人——即便是已经没落的小户,也不应该受这样的折辱。
内监把盛金的木盘捧到淑妃面前,我以为淑妃断然瞧不上如此轻佻的方式,但她只是笑,捡了一枚金掷过去。
淑妃姊姊。我小声说,这样折辱她,不太好……
我闻到她身上淡漠的香气,她的声音也是淡的: 阿韫儿,该你了。
我别过头去,内监有些尴尬地看着皇帝,我不愿意接那枚金锱,世族行止重乎礼,怎么能以赏花楼女人的礼节对待她?
德妃就笑: 谢婕妤是心里有恨,薛昭仪何不说两句好话,看谢婕妤肯不肯赏你?
女人们都哄笑起来,轻纱被穿堂风吹起,是一场荒唐富丽的梦。我终于抓住一枚金,死死攥着,薛昭仪冲我福身,声音软软的: 请谢婕妤赏。
怎么能把自己的尊严扔在地上让人踩?我赌气把那枚金狠狠扔出去,金锱砸中了她的额角,微微泛起一点淤青,然后跌在地上,弹起来,打了两个转。
皇帝抚掌笑了,于是女人们也搅闹着笑,乐姬用白玉一样的手指扫弦,琵琶声里,薛昭仪踩着满地的碎金再次起舞,翻飞的裙袂绽开盛烈的花。
阿韫儿不高兴?淑妃问。
我看着薛昭仪,怔怔地出神: 我不喜欢她,她明知道大家把她当个取乐的玩意儿,还是一味地讨巧谢恩……
后宫中争宠是很常见的事,并不低贱。
我知道,但《懿行传》说『以色侍人者,色衰而爱驰』,又有《诸姬录》云『世族女重德而自爱,耻媚上』……
这是后宫。淑妃打断我,你太年轻, 书看得太多,路走得太少,为人处世的关窍,本就不是书中那般泾渭分明。
但总不应该做个『瓷花瓶』。
那阿韫儿觉得, 女人在后宫最要紧不能丢的是什么?
我本想说自由,但那是不可得的东西, 非但后宫中,天下的男人女人,无不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樊笼里,不能逃脱,不能反抗。
倘若已经没有自由……
尊严,一个人不能连气节风骨都扔在地上任人踩。
尊严?淑妃沉吟片刻, 终于笑了,后宫啊……就是一群美艳的奴才, 奴才又有什么尊严可讲呢?
我那时候并没有吃过什么苦,只是一味读大道理, 并以风骨气节自矜。
我总觉得薛芷费心讨巧又自甘轻贱,实在不是高洁的做法, 很丢世族的气度。我很仰慕淑妃,她过于高贵的出身和清冷的性格满足了我对后宫女人的所有幻想。我只有十四岁, 并不知道有些人拼尽全力只是为了活着。
女人们笑着离去,香料浓郁的气息和月光混在一处, 洒在升平殿空旷冰凉的凿金地板上。
我看见薛昭仪若有若无的眼神,似乎是试探,也像是歉疚。
她们都以为我怨她抢了皇帝,其实我只是恨她把自己的尊严丢在地上任人践踏,踩脏了,就擦一擦, 挤出笑脸,再亲手捧上去求人踩。
我怔怔地站起身, 离开了升平殿,门外明月光华,织神星隔着天河与郎君星相望, 乞巧的缎带飘啊飘,隔着一重门回头看,金樽红纱都寂寞在烛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