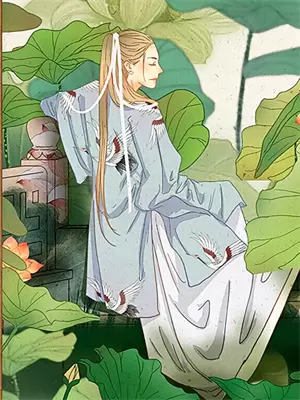等候鸟飞回来小森林
作者: 墨菲的切片面包言情小说连载
《等候鸟飞回来小森林》内容精“墨菲的切片面包”写作功底很厉很多故事情节充满惊严礼阿礼更是拥有超高的人总之这是一本很棒的作《等候鸟飞回来小森林》内容概括:死后重生成黑颈某天竟在领地湖边看到生前男我以为他是来寻连忙勾勾叫跑过谁知下一一个女孩从他车上跳了下亲亲热热扑进他怀两人笑做一?老娘才死一个你就另寻新欢?渣男往你头上拉屎往你头上拉屎1严礼微微侧轻松躲过了我的两次空顺便贴心地把身边的女孩往远处推了免得她被波那女孩美得很灵一头栗色羊毛卷短眼角还缀着颗小小的泪和身高腿长、清冷斯文的严礼站在一...
我以为他是来寻死,连忙勾勾叫跑过去。
谁知下一秒,一个女孩从他车上跳了下来。
亲亲热热扑进他怀里,两人笑做一团。
?
老娘才死一个月,你就另寻新欢?
渣男往你头上拉屎往你头上拉屎
1
严礼微微侧身,轻松躲过了我的两次空袭。
顺便贴心地把身边的女孩往远处推了推,免得她被波及。
那女孩美得很灵动,一头栗色羊毛卷短发,眼角还缀着颗小小的泪痣。
和身高腿长、清冷斯文的严礼站在一起,好一对璧人——
好不爽。
刚刚的奇袭显然让人屎料未及,现在反应过来,女孩哈哈大笑:
阿礼,我怎么觉得它是专门冲你来的
她快活得像只红脚鹬,蹦蹦跳跳回到严礼身边,要帮他摘下发丝间我刚抖落的绒羽。
男人自然地托住她的腰,稍微低头,任由她摆弄——
超级不爽
拜托,还有没有天理。
我只是死了,又不是分手了。
一个月前还哄着我叫了一整夜宝宝,一个月后就和别的女人卿卿我我。
人渣啊,人渣
我忍无可忍,抖着翅膀腾空而起。
两米多的翼展,直接遮蔽住将落未落的夕阳。
往他头上拉屎
2
这次我卯足了劲。
整整 37 泡。
偏偏没有一泡落到严礼头上。
他像是开了闪现,脚下飞转腾挪,动作快出残影,精准躲过了我的每一次高空投翔。
不是……这不科学吧
正巧赶上换羽期,我没法久飞,只好忿忿落回地面,气得 gage gage 大叫。
好在严礼也并不是那么体面。
经过刚刚一番缠斗,我松动脱落的羽毛卷了他满身满头,弄得狼狈不堪。
可他也不恼,拍拍手上的灰便从口袋里摸出一把什么东西,盛放在手心,气定神闲朝我伸来。
嘎挑衅赤裸裸的挑衅
——咦,等等。
是青稞。
他……他怎么知道我爱吃这个
这可是我偶尔飞一趟村里才能得到的稀罕东西。
……算了,好鸟不吃眼前亏。
扑腾半天,我是真饿了。
我走上前,弯下长颈,用又尖又长的喙小心翼翼从他手上啄食。
变成黑颈鹤后,我好像忘记了很多东西。
但我还记得,严礼这双手,是要拿手术刀、要救死扶伤的。
他为这样的理想努力了好久。
我不想真的伤到他。
3
严礼和羊毛卷女孩在湖边的房车营地住了下来。
房车营地正好紧挨着我的领地,我每天划拉着长腿,在他们附近阴暗地爬行。
呵。
我活着的时候忙工作顾不上陪我,我死了倒是有空陪新妹妹度假了。
渣男。
在我的记忆里,严礼工作很忙,非常忙。
他是市三甲医院的外科医生,手术从早排到晚是常态。
就算是难得的假期,也总是接一通电话就得匆匆赶回医院去。
去年我生日的前几天,市郊环城高速上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旅游大巴连环追尾事故。
严礼在手术室连轴转了三天,终于在我生日这天的夜里十一点,脚步虚浮地回到了家。
他说想给我庆生,要我一定在家等他。
可人是被我等回来了,我跑去厨房端蛋糕,再回到客厅时,他却已经坐在沙发上睡着了。
外套都还没脱。
看着他憔悴的脸色,和鼻梁面颊上尚未消去的口罩压痕。
我实在不忍心叫他。
凌晨一点半,严礼猛地惊醒过来。
对不起,宝宝。他挣扎着坐起身,声音里还带着浓浓的倦意,我睡了多久?
眼看他要转头去看表,我飞快地伸手捧住他的脸,急切道:
别道歉啦,马上就过零点了,快祝你亲爱的女朋友生日快乐
那双布满血丝的眼中的懊恼稍稍淡去了一点。
严礼倾身过来抱住我,郑重地亲了亲我的眼角:
生日快乐,宝贝,我爱你。
抱歉,今天太累了,等忙完这几天,我一定好好给你补……
一句话没说完,他又靠着我睡了过去。
第二天天还没亮,严礼就又起床去上班了。
半梦半醒间,我感觉有人在我唇畔小心地印下一吻,接着,传来一句轻轻的对不起。
其实之前严礼刚告诉我,他们医院会接收大部分车祸伤者的时候,我就提议,这几天他免不了要加班,所以我的生日他不用特意准备什么,只要陪我在医院食堂吃顿便饭就好了。
毕竟我也没什么仪式感,这样还能省下一两小时的通勤时间,让他在办公室多睡一会儿。
但严礼坚决不同意把我的生日过得这样随便。
他在我最喜欢的餐厅订了位子,让我先和朋友出去庆祝,等他晚上回来陪我切蛋糕。
本来是很完美的计划。
当然,我并不怪他。可第二天早晨醒来,看到床上空荡荡的另一半,说不失落是假的。
我懒洋洋地在被子里固涌固涌,去摸闹铃响个不停的手机。
忽然,被什么银色的东西晃了下眼睛。
迷迷糊糊抬起手。
啊是我之前在小某书收藏的设计师款手链
我每天在小某书收藏百条帖子,严礼那么忙,我真没想到他会看到这个。
更何况这位设计师的作品,每一件都是孤品,有市无价,相当难买。
我在新手链上吧唧亲一口,一个鲤鱼打挺弹射起床,美美拍了张戴手链的照片,发给置顶的AAA 没空陪女友切蛋糕的超级大忙人:
爱你哦
4
但现在不是很爱了。
真的。
严礼和羊毛卷住在湖边,每天不干别的。
羊毛卷架着长枪短炮观鸟。
严礼坐在旁边含情脉脉地看羊毛卷。
不是。你们很闲吗?
能不能离开这里,去做一些只有人类才能做的事?
比如上班、上班、上班。
这片湖边湿地倒是有各种各样的鸟,长嘴百灵、白骨顶鸡、斑头雁、黄头鹡鸰……
国一的黑颈鹤就有两百多只。
看去吧,谁有你们会看啊。
6 月,正是育雏的时节。
眼下各种鸟类的幼雏争相破壳,做父母的个顶个地护犊子,湿地上每天火药味重得很。
白天看着同类吱吱喳喳地打架、脖颈交缠地秀恩爱,晚上鸟睡了,又得看我背信弃义的前男友和新欢搂在一起看星星。
看着严礼轻轻地吻羊毛卷眼角的泪痣。
还真是怪浪漫呢。
草滩上的草不知不觉间被我狠狠啄秃一大片,这日子是一天都过不下去了。
5
终于熬过换羽期,我鸟不停翼地飞离了这个是非之地。
我的目的地,是个二十多公里外的小村庄。
叫村庄其实并不准确。
湖泊周边水草丰美,历来是本地牧民的夏季牧场。
每年初夏,天气回暖,几户牧民赶着牦牛转场过来,就地搭起白布帐房,挂好五彩经幡,便形成了一片松散的小聚落。
重生成黑颈鹤后,我和其他忙着求偶筑巢的同类总是没什么共同语言。
高原湖泊壮阔的景色看久了,也不免觉得自己渺小又孤单。
于是我时不时就离开领地四处闲逛,就这样发现了这个人类聚落。
第一次来时,有两个年轻人在草场上放牛。
其中一头牛像是受了惊,正往远离牛群的地方狂奔。
放牛人甩着抛石绳,狼狈地在后面追。
我路见不平,一个俯冲截住了牦牛的去路。
牦牛惊得急刹车,终于被人套住,乖乖归了群。
这只是卓玛婆婆的,幸好没事。
两个年轻人在地面上冲我挥手,谢谢你——黑颈鹤——
听说黑颈鹤是藏族的神鸟,不知是不是被长久信奉的缘故,现在的我,竟然能听懂藏语。
我有些惊奇,盘旋在空中,远远跟着放牛人回了村子。
放牛人口中的卓玛婆婆,是个头发花白、皮肤黝黑,背脊有些佝偻的藏族老婆婆。
听到是天降仙鹤截住了她的牛,老人家又惊又喜,简直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最后从粮袋里倒出一大捧青稞来,盛在碗里招待我。
借着神鸟的名头,我美美饱餐一顿。
可吃完抬头一看,我却有些后悔了。
老婆婆家明显并不富裕,粮袋干瘪,帐房里家徒四壁。
放牛的年轻人把她的几头牛赶来后就离开了,眼下老婆婆正弓着腰费力地拴牛,每拴一头,都要停下来歇很久。
她好像是独自生活的。
我突然觉得好过意不去。
于是,从那之后,我时不时就来村子里一趟。
牧民们都很虔诚,见到仙鹤降落自家门口,都愿意拿出干粮招待我。
我吃一点,然后衔来纸片或布头,示意人类打包带走。
然后再把包好的粮食叼到卓玛婆婆家去。
招摇撞骗,连吃带拿。
可牧民们不仅不对我人人喊打,还纷纷笑逐颜开,说我有灵气、通人性,当真是无量光佛显了灵。
嘿,这神鸟还真好当。
来过几次之后,我发觉人们也开始自发地给卓玛婆婆送些糌粑、酥油一类的吃食。
婆婆不收,就笑着指指天上:
您就收下吧,这次是仙鹤让送的——看,祂又来了。
6
其实一般情况下,卓玛婆婆的村子并不属于黑颈鹤们会经常造访的区域。
因此,当我来过两次后,牧民们便有些担心,以为是我的雏鸟出了意外。
再后来,见我每次飞来都是孤身一鸟。
我在村中的鸟设就变成了——
丧偶。
卓玛婆婆心地纯善,对我丧偶的遭遇尤为同情。
而来这里客串神鸟的次数多了,我也陆陆续续从人们口中,拼凑出了卓玛婆婆的过去。
早年丧夫,有个独子。
一生要强,偏偏儿子是个不争气的,人到中年依旧没个正形,平时在附近的县城游手好闲,既没有正经工作,也不肯回来帮老母亲干活。
卓玛婆婆勤劳肯干,但终究年老体衰,家里的牦牛越养越少,日子也越来越拮据。
偶尔偏头疼或关节炎发作,痛得下不了床,临近的村户清晨见婆婆没出帐房,便会帮她放牛。
一次我飞来村里时,卓玛婆婆又犯了老毛病,正独自坐在帐房门口,阖眼摇着转经筒诵经。
午后阳光正好,天空湛蓝,白色的帐房外,草原尚且嫩绿,毛茸茸地开满一层黄色小花。
婆婆和我已经很相熟,听到我来,她照例给我盛了一小碗青稞,一边看着我吃,一边慢慢对我讲话。
黑颈鹤啊,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母亲教过我一句谚语。
『人的痛苦只是一年,鸟的痛苦却是一辈子。』
人的家人、爱人死去,他痛苦一年,也就忘了,可鸟,是一辈子不会忘的。
鸟的配偶死去,它一辈子都不会再找其他鸟,最后会心怀痛苦地死去。
草原上忽地卷起劲风,我停下啄食,抬起脖颈望向她。
风吹乱了卓玛婆婆花白的鬓发,但她浑然未觉,只是看着我,眼里满是悲悯:
独来独往的黑颈鹤啊,你现在也在痛苦吗?扎西告诉我,第一次见到你时,你直直往发狂的牦牛面前飞,这样才拦住了我的牛。
黑颈鹤,就算失去所爱,也请你一定不要去寻死。三宝造福,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
婆婆阖上有些浑浊的眼睛,转动转经筒,虔诚地为我诵经祈福。
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我被一种巨大的悲恸击中了。
我忽然觉得喘不上气,胸腔深处一阵钝痛,像被牦牛踏了一脚。
我抖抖翅膀,不知所措地叫了两声。
明明我并没有丧偶,严礼现在活得好好的呢。
对他来说,死的人是我。
是他丧偶了才对。
不过我是怎么死的来着?
想不起来。
所以,严礼只会为我的死痛苦一年吗?
婆婆丧夫多年,她已经不会为此感到痛苦了吗?
或许……这样也好。
——至少,在严礼和羊毛卷出现在湖边之前,我真是这么想的。
7
昏黄的暮色里,我飞得极快,直向卓玛婆婆家去。
说真的,痛苦一年我完全可以理解。
毕竟死人还是别对活人有太强的占有欲。
可我刚死一个月,严礼就带新女友亲亲热热地出来度假,丝毫看不出伤心的痕迹。
这未免也太快了点吧?
我们高中相识,大学在一起,到我去世时,已经交往了七年。
七年啊,他不到一个月就把我忘了?
而且,仔细想想。
这段时间,他们一直待在这远离人烟的地方,白天自己生火做饭,晚上就睡在房车里。
哪有情侣刚在一起,就约条件这么艰苦的会啊?
更别说我每天看得真切,那二人相处起来和谐默契、融洽无间,说是一起生活了很久都不为过。
所以。
在我去世前很久,严礼就已经背叛了我吗?
这是唯一说得通的解释。
他骗了我多长时间?
我不知道。
我本就遗忘了很多东西。
偏偏我能记起的,还都是严礼最好的样子。
穿着高中校服和我谈论理想的他;
第一次穿上白大褂,迫不及待打视频给我,却又在接通后忽然害羞的他;
在花树下向我告白,得到肯定答复后开心得红了眼圈的他;
规培累到生病却依然眼里有光的他;
跨年烟花下,在拥挤的人潮中紧紧牵着我的手,在无人的露台和我接吻的他;
每天早晨醒来后,第一眼看到的近在咫尺的他。
从哪一幕起,他心里就悄悄住进了别人?
该死的,为什么该想的想不起来,非要想起这些让人心烦意乱的东西?
我恼火地用力扇动翅膀,恨不得把所有记忆都甩在身后。
飞到村里时,夕阳即将沉落,牦牛已经归圈。
卓玛婆婆正坐在帐房外的矮凳上做酥油。
我心里不爽得要命,落地就伸长脖子,对着天嘎嘎大叫。
卓玛婆婆手里揉捏着酥油块,温声道: 黑颈鹤,你来啦。
我扑棱着翅膀跳脚: gage gage
饿不饿?等一下,婆婆现在腾不出手。
gage gage
今天吃饱啦?
gage gage
婆婆终于停下手里的活,抬头看看我。半晌,试探地问: 受委屈啦?
嘎。我不跳了,小声地叫。
卓玛婆婆轻轻笑起来。
她在抹布上蹭蹭手,起身回帐房倒了一碗青稞,摆在离我不远不近的地上,便又回去做酥油。
桌上的白铁皮盆里,酥油已经凝固成乳白色的面团状。婆婆把大团分成小团,又把小团慢慢拍打成易于码放的圆饼。
她一边拍,一边就着节拍咿咿呀呀哼起了歌。
就像在安慰哭闹的小孩子。
黑颈鹤,黑颈鹤,洁白的仙鹤啊,请把双翅借给我。
不到远处去飞,绕湖一圈就回。
昼夜永顺利,三宝佑吉祥……
迟暮的草原上,日光正在一寸寸暗下去。
近处的几顶白布帐房升起炊烟,渐次透出暖色的灯光。
悠扬轻快的旋律里,我的世界好像忽然变得很小,小到只剩下身后窸窸窣窣吃草的牛群,和面前慈爱地唱着歌的老婆婆。
心头的烦躁渐渐止息。
如果能一直待在这里就好了,我忍不住想。
婆婆,我再也不想回去了。
最近几天气得一直没有好好觅食,现在放松下来,肚子才觉得饿。
我埋头吃了点东西,然后弯曲脖颈去梳理一路上被吹乱的飞羽。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一辆从未见过的摩托车,停在帐房侧面。
8
原来卓玛婆婆这么急着做酥油,是因为她的儿子回来了。
我收回目光,恰好看到一个吊儿郎当的瘦削男人,嚼着肉干从帐房里走出来。
帐房篷布裹了风,猎猎作响。
妈,好了没?快点,晚上有人叫我喝酒。
你去拿袋子吧,马上做完——
对了妈,你把钱放哪了?我没钱了……嚯,这就是扎西说的那只什么长颈鹤?这么大。
男人停住脚,上下打量着我,面露惊奇。
看了一会儿,他露出个意味不明的笑,弯腰从地上抓起一把砂石,向我勾勾手:
仙鹤,仙鹤,快过来,我有好吃的给你。
我站着没动。
从看到这男人的第一眼,我就有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恐惧,厌恶,甚至是……憎恨。
为什么?我理应从未见过他。
肌肉下意识地绷紧,心脏像被一只冰凉的手攥住,心跳一下重过一下。
这畜生还挺聪明。
见我没反应,男人无聊地撇撇嘴。
卓玛婆婆手上忙着,闻言看过来。
——达吉快把石子放下看清他掌上的东西,婆婆惊得摆手,别说金尊玉贵的神鸟,就是普通的鸟,吃多了石子也是要穿肠烂肚的
知道了知道了。被叫做达吉的男人敷衍着,眼睛依旧紧盯我,嗤笑一声,它要真是神鸟,还能怕几颗破石头?
我几乎没听他们在说什么,只觉得太阳穴在一跳一跳地抽痛。
好像有个声音附在我耳边,说我忘记了某些重要的东西……某些绝对不该被遗忘的东西。
——这一次,决不能遗忘的东西。
余光里,最后一缕日光无声地熄灭了。
面前空无一人的白布帐房,兀自亮起灯光。
那灯光昏暗惨白,半明半昧,却清晰地映出达吉眼侧,一道蜿蜒至眉骨的短疤。
我神思恍惚,仿佛看到眼前男人的脸孔倏然变得狰狞扭曲、目眦欲裂,额头上青筋根根暴起。
他手里应该高举着什么东西,嘴一张一合,胸膛起伏着,像在歇斯底里地叫喊。
但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他在说什么?
风声消失了,牛群低沉粗粝的叫声消失了。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四下一阵怪异的静寂。
不对。
风还在吹。
是我的耳朵,忽然听不见东西了——
唰啦
我浑身一震,向后惊跳几步。
达吉把掌心的石子随手一扬,洒在了我脚边。
白布帐房没有亮灯,仍隐没在黑暗里。
我心跳得厉害,但也顾不得眼前景象,振翅而起,直接向湖边营地的方向飞去。
我必须马上赶回严礼那里。
否则,就会发生无可挽回的灾祸。
不知为何,这样的想法无端浮现在我脑中。